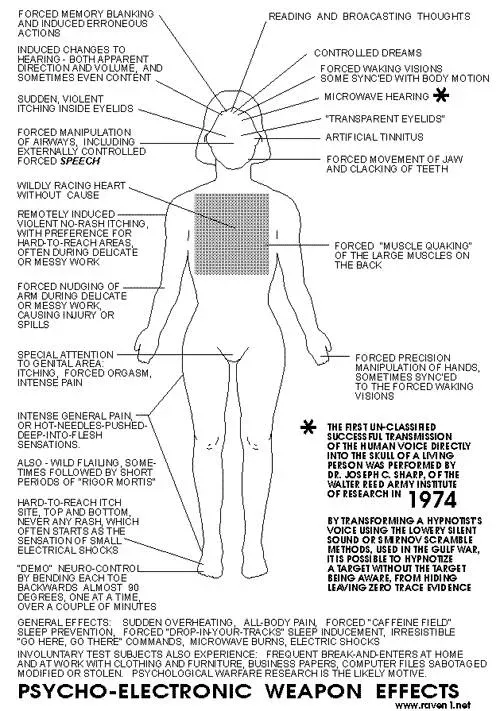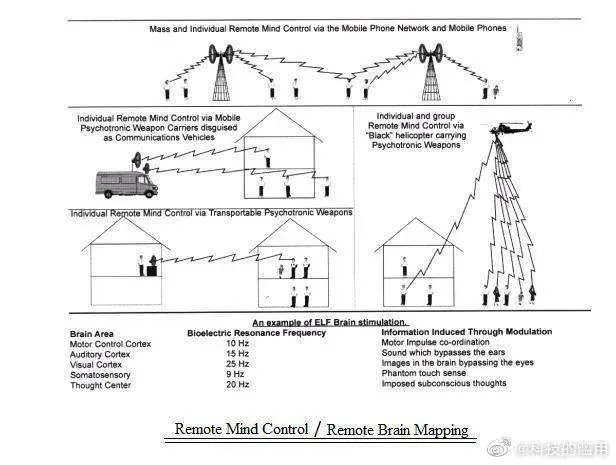「物聯網」(Internet of Things,縮寫IoT)一詞誕生於15年前,最近幾年,這個「高大上」的事物逐漸走進我們的生活。物聯網能夠將特定空間環境中的所有物體連接起來,進行擬人化信息感知和協同交互,而且具備自我學習、處理、決策和控制的行為能力,從而完成智能化生產和服務。當前,物聯網正在推動人類社會從「信息化」向「智能化」轉變,促進信息科技與產業發生巨大變化。不久的將來,物聯網將有力改變我們生活與工作的環境,把我們帶進智能化世界。
物聯網技術思想是「按需求連接萬物」
在2005年信息社會世界峰會上,國際電信聯盟正式提出「物聯網」概念,提出無所不在的「物聯網」通信時代即將來臨,世界上所有物體,從輪胎到牙刷、從房屋到紙巾都可以通過網際網路主動進行信息交換。
物聯網的技術思想是「按需求連接萬物」。具體而言,就是通過各種網路技術及射頻識別(通過無線電進行數據交換以達到信息識別)、紅外感應器、全球定位系統、激光掃描器等信息感測設備,按照約定協議將包括人、機、物在內所有能夠被獨立標識的物端(包括所有實體和虛擬的物理對象及終端設備)無處不在地按需求連接起來,進行信息傳輸和協同交互,以實現對物端的智能化信息感知、識別、定位、跟蹤、監控和管理,構建所有物端之間具有類人化知識學習、分析處理、自動決策和行為控制能力的智能化服務環境。
信息社會正在從互聯網時代向物聯網時代發展。如果說互聯網是把人作為連接和服務對象,那麼物聯網就是將信息網路連接和服務的對象從人擴展到物,以實現「萬物互聯」。二者在需求滿足上也有所區別:互聯網時代,信息網路的任務是滿足公共信息傳輸需求;物聯網時代,信息網路的任務是滿足特定智能服務需求,二者相互支撐,不可或缺。
物聯網環境下未來的智能服務系統,將成為未來社會重要的基礎設施。智能服務系統作為物聯網科技創新的關鍵,將真實環境物理空間與虛擬環境信息空間進行映射協同,實現通信、計算和控制的融合。智能服務系統使物與物、人與物之間能夠以新的方式進行主動的協同交互,從而鉤織一張物理世界內生互聯的智能協同網路。
重塑生產組織方式,推動產業革命
物聯網已成為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的重要驅動力。歷經概念興起驅動、示範應用引領、技術顯著進步和產業逐步成熟,物聯網正加快轉化為現實科技生產力。如果說影響生產工具和產品的技術會帶來量變,那麼物聯網技術將帶來質變,因為它將重塑生產組織方式。物聯網科技產業在全球範圍內快速發展,正與製造技術、新能源、新材料等領域融合,步入產業大變革前夜,迎來大發展時代。
隨著物聯網應用的普及,不同應用需求如智能可穿戴設備、智能家電、智能網聯汽車、智能機器人、智慧醫療、農田水利、市政建築等數以萬億計的新設備將接入網路。這些應用正在爆發性增長並將形成海量數據,促進生產生活和社會管理方式進一步智能化、網路化和精細化,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更加智能高效。
與其他高新技術融合發展是物聯網技術的重要特性。當前,物聯網正促進5G、窄帶物聯網、雲計算、大數據、人工智慧、區塊鏈和邊緣計算等新一代信息技術向各領域滲透,引發全球性產業分工格局重大變革。在組網方面,全球範圍內低功率廣域網技術正快速興起並逐步商用,面向物聯網廣覆蓋、低時延場景的5G技術標準化進程加速。同時,工業乙太網、短距離通信等相關通信技術快速發展,為人、機、物的智能化按需組網互聯提供良好技術支撐。在信息處理方面,信息感知、知識表示、機器學習等技術迅速發展,極大提升物聯網的智能化數據處理能力。在物聯網虛擬平台、數字孿生與操作系統方面,基於雲計算及開源軟體的廣泛應用,有效降低企業構建生態門檻,推動全球範圍內物聯網公共服務平台和操作系統的進步。
物聯網帶來數字化和智能化變革,可以改變許多行業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概念,莫過於「工業互聯網」。2011年,「工業4.0」概念由德國首次提出後,至今已有多個國家跟進。美國通用電氣公司提出的「工業互聯網」概念是全球工業系統與高級計算、分析、感測技術及互聯網的高度融合,意思是在物聯網基礎上將人、數據和機器連接起來,讓設備、生產線、工廠、供應商、產品和客戶相互間緊密地按需協同,綜合應用大數據分析技術和遠程控制技術,優化工業設施和機器的運行維護,通過網路化智能化手段提升工業製造智能化水平,形成跨設備、跨系統、跨廠區、跨地區的互聯互通產業鏈,從而提高效率,推動整個製造服務體系智能化。工業互聯網作為中國智能製造業發展的重要支撐,已經得到我國政府高度重視,「十三五」規劃、《國務院關於積極推進「互聯網+」行動的指導意見》、《關於深化製造業與互聯網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》都明確提出發展工業互聯網。
由於前景可觀,世界各國都在加速搶佔物聯網產業發展先機。在產業層面,相關大型公司紛紛制定物聯網發展戰略,並通過合作、併購等方式快速進行重點行業和產業鏈關鍵環節布局,提升在整個產業中的地位。阿里巴巴、騰訊、百度、亞馬遜、蘋果、英特爾、高通等全球知名企業,均從不同環節和層面布局物聯網。
智能生產、智慧生活正在開啟
物聯網的發展為人類社會描繪出智能化世界的美好藍圖。那麼,從抽象概念回到具體應用上來,物聯網究竟怎樣與我們的生產、生活發生聯繫?
目前,物聯網的實際應用,已在製造業、農業、家居、交通和車聯網、醫療健康等多個領域取得顯著成果。目前全球活躍的物聯網終端設備數量已超過500億個,萬億級垂直行業市場正在興起。
生產方面,物聯網對工業、農業影響深遠。工業互聯網環境目前可以從網路連接的終端設備處獲取和分析數據,結合遠程監視和控制設備監控工業系統,可以實現各種具有感測、識別、處理、通信、驅動和聯網功能的製造設備的無縫集成。通過射頻識別等技術對相關生產資料進行電子化標識,實現生產過程及供應鏈的智能化管理,利用感測器等技術加強生產狀態信息的實時採集和數據分析,提升效率和質量,促進安全生產和節能減排。
在智慧農業領域,物聯網助力「精耕細作」。通過收集種植環境的溫度、降雨量、濕度、風速、病蟲害和土壤含量的數據,實現耕種智能處理和決策。甚至可以將物聯網獲得的數據應用於精確施肥計劃,最大程度地減少風險和浪費,同時減少管理農作物所需的工作量。
在生活中,家居、交通、醫療健康等都是物聯網的用武之地。智能家居將信息技術與室內物品設施、人的室內生活、安全防護等各方面融合協同,推進家居、安防服務信息化、智慧化。比如語音控制可以幫助視力不佳或行動不便的用戶,警報系統可以連接到用戶佩戴的人工耳蝸,監控系統還可以對跌倒或癲癇等健康事故進行報警。智能交通和車聯網也離不開物聯網技術。在不同要素間無縫連接,能夠實現車內和車外通信、智能交通控制、智能停車、電子收費系統、車輛管理控制等多種場景應用。比如在物流車隊管理中,通過無線感測器查看貨物的位置和狀況,並在異常時發送警報。智慧醫療利用物聯網技術,可以實現對藥品保健品的快速跟蹤和定位,降低監管成本;通過建立臨床數據應用中心,可以開展基於物聯網智能感知和大數據分析的精準醫療應用;也可以充分運用智能穿戴設備(智能手環、智能指環等)和射頻識別等技術採集居民健康信息,建立健康大數據創新管理雲服務平台。
物聯網已經成為全球信息科技發展的重要趨勢之一,它的出現和興起為我國科技和經濟發展帶來難得機遇。我們應當抓住機遇創造未來,建設好智能化數字中國。
(作者為中國通信學會物聯網委員會主任)
轉自:
http://it.people.com.cn/n1/2020/0317/c1009-31635058.html